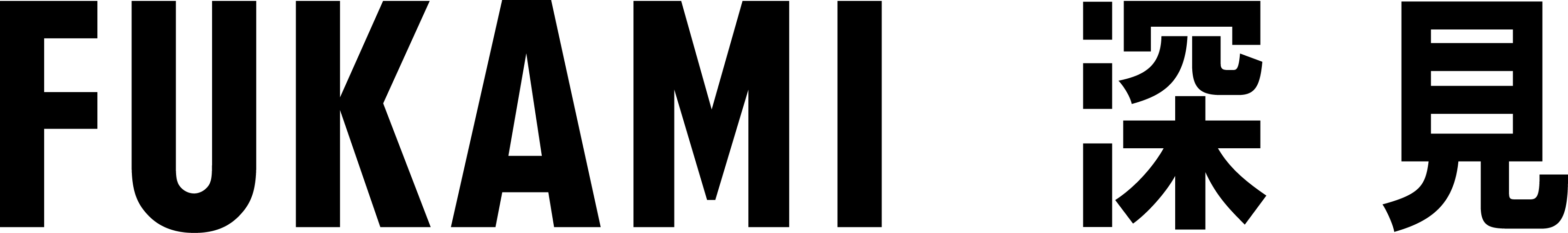很多電影在英國的上映日期都比香港或台灣來得晚,但《The French Dispatch》卻是例外,能夠在首映日三天後就看到這部期待已久的電影,而且是在Barbican的大螢幕上,也算是週日的小確幸。
從頭到尾,這都是一部引人入勝的電影,由一本法國小鎮週日晚報的主編之死,引申出三個有趣的、鮮為人知的,甚至可以說是奇情的故事,關於藝術、自由、美食,關於愛。
導演Wes Anderson標誌性的色調與構圖依然帶領著電影的主旋律,然而在視覺上,這部作品有更多細節處使我著迷,比如遊走在黑白與彩色之間的畫面;比如在佈景、視覺上加入許多紙的質感——在採編房壁報板上整齊排列的報導主題及進度、充滿主編字跡和評語的稿件,當然少不了打字機的聲音和有趣的插畫。

我中學時期的理想的就是當一名記者,為了夢寐以求的傳理系的面試,我做了一個作品集,調查了一些香港鮮為人知的故事,然後用自己的文字報導出來,回想起來那確實是非常稚嫩的作品(至少當日在我面前的教授是這樣認為,事實上,他連作品集都沒打開就叫我離開)。可想而知,我並沒有如願靠近理想的學系,但畢業前倒是有一家報館願意給我一次機會,因為家庭的因素,我又與那個機會擦身而過。從此我對新聞從業員有著更深的感受——他們不但有才華、有拼勁,往往還是以與能力不相配的低薪支撐著夢想。
因為個人的偏好,後來為不同公司創作內容時,我總希望能夠加入報導類的文字,比如一些藝術家專訪,或者是關於世界各地的美食、建築物、小店背後的小故事,對我來說說故事比一切都吸引。之前為前公司設計了一本小雜誌(zine),老闆跟我有一樣的渴望,我把小雜誌的創刊號打印出來,放在她的桌子上,她拿起紅筆修改,這樣來回了幾遍,有了初稿、二稿、三稿,我們終於一嚐辦紙媒的滋味,雖然就只有那麼一次,雖然大部分同事似乎不理解我們的熱忱,但也成為了我在那份工作中最快樂的回憶。
而在觀看電影的過程中,我想起了那些片段,我想著這部電影之所以如此特別,是因為它並不是著重於交代上一代的人如何做新聞,而是是跑新聞的過程中的快樂。三個奇幻的故事看似並不相關,劇情更是朝著一發不可收拾的角度進發,當往往在頻臨失控時,導演能給每個故事一個精準的落點,一個餘韻無窮的落點。
雖然電影設定在法國小鎮,但Wes Anderson在勾勒人物、劇情、場景時,腦中想的卻是美國雜誌The New Yorker——一本結合新聞、小說、漫畫、美食、政治的雜誌,跟The French Dispatch同樣在1925年誕生。The New Yorker或許是世界上第一本新聞與生活的界線的報刊,把生活變得認真,把政治變得幽默,而當中的secret recipe,非才華洋溢的記者和編輯們莫屬,因為他們總能找到小故事中的趣味和人情味,他們總是在創造而非跟隨(畢竟他們是第一個刊登村上春樹作品的歐美媒體,為此村上一直心存感激)。
隨著主編去世,這個越看越有味的故事就在觀眾的不捨中落幕,感動的同時,看到主編房的標語”No Crying“,想起香港曾經存在過的紙媒,想起記者們拿著最後的報紙在雨中和大家道別,想起小時候跟父母上茶樓看報紙(當時還特別為我買一份《兒童快報》)的日子,這些年來失去的事物都湧上心頭,又怎能不哭啊。
後記:
最近一直在想,到底什麼是做「內容」,很多主流媒體、雜誌現在都講求速度,轉發其他媒體的「新聞」(新聞過了一小時就變成舊聞),很多我有留意的時尚雜誌,發布的內容跟內容農場無異,「內容」的內容其實一點內容都沒有,越想越覺得詭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