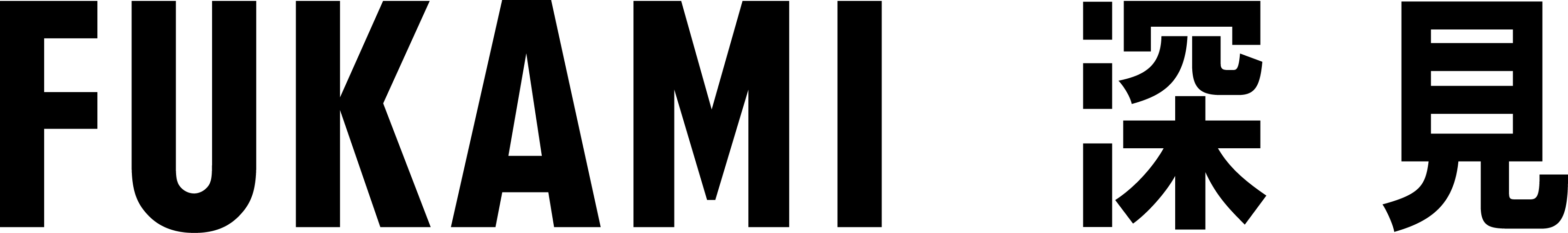那年六月獨遊東京八日,或許因為我是獨生女的關係,自己一個旅遊比我想像中簡單。每當我獨自一人提著行李箱到達機場準備出發時,總覺得特別暢快,那不單單是對旅程的期待,也是對自由的盼望。
他說他也喜歡東京,叫我多傳照片給他看,我拍下了鎌倉的海、輕井澤的教堂、淺草寺、代官山,還有許多有趣的小地方,跟他分享,他總會用既羨慕又妒忌的文字回應。
在東京的某一晚,他說他坐立不安,因為快將知道他這個學期的成績,而成績將會決定他考不考得上法律文憑,而法律文憑則是當律師的門檻。我叫他不用擔心,我會替他去淺草寺許個願。晚上的淺草寺很寧靜,寺院的燈籠都亮起來,而走道兩旁的商店都關上門,走往大殿的路忽然變短了,時間卻又似乎變得更漫長,好像大殿後面藏著另一個時空。
那天晚上十二點,他打來說他的成績剛好夠過,他好興奮,一直叫一直笑,然後深一口呼吸,用比較冷靜的語氣說了一聲謝謝。那是他第一次打給我,也應該是我們(在我的印象中)第一次真正的用言語交談,他的聲音比我想像的低沈。我忘了當下說了些什麼,大概就是恭喜他跟陪他笑之類的。
那天晚上,我們又用文字聊到深夜,也許是因為他如釋重負的關係,我們的話題也比以前的輕鬆。
他問:「你有什麼怪癖?」怪癖或許沒有,又或許我不想告訴你,但壞習慣還是有許多。「例如呢?」我不喜歡喝水。「天啊,好不健康,但我也是。」我以前吃麥當勞喜歡要許多番茄醬然後一包一包的吸。「同好,煉乳也很好吸。」哈哈,我也喜歡吃煉乳。「我問你一個很認真的問題,你喜歡有顆粒的花生醬還是沒顆粒的。」沒顆粒的,滑滑的好吃。「連這個也一樣,真不懂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有顆粒的。」
然後我們又花了一個小時談cult片,再花了一個小時談音樂,口味還是如此的相似。
不知不覺天已經亮了,他說他也不睡了,乾脆去弄一個早餐,他煮了味噌湯、白飯,還有一些肉和菜,我說這個早餐未免太豐富了吧,他說:「因為你在日本,我也想吃一點日本料理。」
那八日七夜,雖然自己一個人到處遊玩,但電話的另一端也同時聯繫著另一個人,感覺其實不太像獨遊,倒是像真的有伴。他就像《Her》裡的Samantha,一個只能透過聲音和文字交流的卻有真摯感情的「人」,我忘了他六年前長什麼樣,而我也不在乎他現在長什麼樣,六年來我們的生活不是沒有重疊(例如我們在同一個圈子玩,例如我們唸同一家大學),但我們也確實沒什麼交集,無論如何,他還是跟我心靈最接近的人。
Theodore: What are you doing?
Samantha: I'm just sitting here, looking at the world and writing a new piece of music.
Theodore: Can I hear it? What's this one about?
Samantha: Well, I was thinking, we don't really have any photographs of us. And I thought this song could be like a photo that captures us in this moment in our life together.
Theodore: Aw, I like our photograph. I can see you in it.
Samantha: I am.
然後他傳了一條錄音給我,是他自彈自唱的Coldplay的Parachutes,吉他聲很輕,歌聲很柔,而聲線也真的跟Chris Martin有點像。我說他唱得真好,他卻回應說這首歌只有四十幾秒,因為歌短,所以總能好好掌握。
我總覺得他在暗示些什麼。
In a haze, a stormy haze
I'll be round I'll be loving you always, always
Here I am and I'll take my time
Here I am and I'll wait in line always
Always